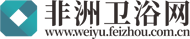外婆的银匠湾
文/黄淳
今年是老外婆126周年诞辰,她老人家去世几十年了,我仍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到乡下看望她时所经历的几件往事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其一,寿材当床
老外婆住在内江田家场乡下的银匠湾。那年月,内江城只有一条土石公路通到田家场,客运班车很少。到银匠湾没公路,我和几个表弟表妹同去看望老外婆。为了节约几角车票钱,我们选择了从城里步行到银匠湾。二十多里石板小路,翻山越岭走了大半天,终于走到了银匠湾。一时来了这么多小孙辈,外婆既高兴也犯愁。高兴的是外孙们来了,小小的寒舍热闹了;犯愁的是只有一张木架床,这么多人怎么睡得下。她转身一看,进门左侧靠墙木凳上的寿材,情急之下,不得不用它以解一时之急。
内江乡下都是这习俗,老年人上了年纪,就要添置一副寿材,以备不时之需。乡下普通人家的寿材,多是用几块厚杂木镶拼而成,不用油漆,密封好,平时装粮食等物品不被鼠害。外婆的寿材也是这种。听说要把它当床,我们觉得很好玩,人人都争抢着要去睡。后来协商的结果是都可以睡,但要排轮子。记不住我排在第几了。当然,上去睡,寿材盖是敞开的。一个人睡在里面,比睡大木床舒服。因为,大床睡的人多,拥挤摆不开,手脚伸不开,很难受。一人睡寿材舒坦,所以人人争抢,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好在老外婆知晓孙儿们的小心眼,立即居中裁决,挨轮子排位,让大家心服口服。
就这样,寿材当床,解决了我们睡觉难题,也让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。
其二,红苕烧仔鸡
银匠湾的夜幕降临了。初时,木板墙外的蟋蟀啾啾鸣叫,池塘深处的青蛙不甘示弱地随之伴唱,偶尔传来几声拖长了音调的犬叫。夜深了,银匠湾寂静了下来,虫不鸣,蛙不唱,狗狗也入睡了。
突然间,墙角木鸡笼传来凄厉的哀叫。外婆立即翻身起床,顺手抓起灶边的一根马桑杆,一边挥舞,一边呼赶,去、去、去。我被惊醒了,但迷迷糊糊的,不知出了什么状况,一会儿,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第二天早上,起床后,看到陶土缸钵里装了两只去了毛的鸡崽,再看鸡笼,两只小鸡崽不在里面了。
外婆说,昨晚,门缝里钻进来一只黄鼠狼,咬坏了一只鸡仔。还好,没被它拖走。我问,为啥缸钵里是两只鸡。外婆说,你们来,还没打过牙祭,反正少了一只鸡,另一只也不好喂,干脆都宰了,让你们打一顿饱牙祭。
两只鸡崽,打整干净了,也不到两斤肉。外婆削了几个红苕,切成方块,烧在鸡肉里。端上小桌子,香香的味道让我们垂涎欲滴。大家抓起筷子,你一块我一块,你一坨我一坨,一会儿就要见底了。
外婆见我们抢得欢,高兴得笑眯了眼,还问我们,好吃不。我夹了一块递给外婆,说:“外婆你尝尝,真的好好吃哟。”外婆揺摇头说:“你们吃,你们吃,我吃过了。”
红苕烧仔鸡,鸡块、红苕、老姜、井盐巴、干海椒,最传统的柴火顶锅灶烹饪方法,最简单的食材,在外婆手里转化成了天底下最美味的菜肴。
现在想起来,那钵红苕烧仔鸡,不仅仅是味美,更承载着老外婆对我们晩辈的一片深深的爱。还有,外婆说吃过了,肯定不是真话。她老人家为了让我们多吃点,自己肯定舍不得动筷子夹鸡肉,最多用匙子尝尝了味道咸淡。
外婆的良苦用心,是她慈祥、和善质朴情怀的本能体现。她感动着我,我会永远铭记在心。
其三,梁拾家的连渣闹
梁拾,是银匠湾外婆家邻居梁大娘的儿子,与我们年龄相近。我们来到银匠湾,梁拾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,带我们到山坡上折马桑枝,和我们一起在银匠湾水塘钓小鲫鱼。
外婆告诉我们,梁大娘要做连渣闹招待我们。我没听过,更没吃过,迫不及待地问:“外婆,啥子连渣闹?”梁拾在一旁说:“哟,哟,哟,连渣闹都没吃过!”外婆说,“连渣闹,就是用豌豆磨粉做成的凉粉。乡下人节约,豌豆磨粉不过滤豆渣,连豆渣做成的凉粉就叫连渣闹。”
那年月,做连渣闹也不是常事,有客来,或者过年过节才做。外婆与梁家邻里之间和睦相处,做啥好吃的,也会邀请来尝尝。我们来银匠湾,梁大娘做连渣闹,让我们尝尝鲜,是托外婆的福,也是外婆平时积德留下的善缘。
连渣闹很好吃,很有特色。乡下没醋没酱油,更没味精鸡精,就用火烧生海椒剁碎,加盐加葱蒜作调料。带豆渣的凉粉,切成长条块,微绿淡黄透亮,不加调料时,飘溢出一丝淡淡的豌豆黄清香。浇上调料,粗中带滑的粉块入口即有豌豆原汁原味的鲜香。一碗下肚,还想第二碗。
这种原生态乡间连渣闹,如果放在今天去登大雅之堂,编出些乡愁故事,吸引食客品尝,一定会大受欢迎,一定会卖出个好价钱。遗憾的是,从此后,再也没有吃过这种银匠湾连渣闹,也不知梁大娘的这一绝技后人是否传承了下来。
几十年后,再到田家场,公路修到了银匠湾村头,自驾车去很方便了。乡间的残檐破屋没了踪影,田垄竹林边伫立起了幢幢砖混小楼。只是外婆不在了,脑海里留下的还是银匠湾那些老屋,还有记忆犹新的那些银匠湾往事。
2023年3月31日
(作者系江津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)
编辑:朱阳夏
责编:陈泰湧
审核:万鹏